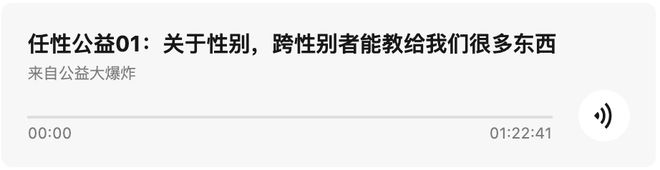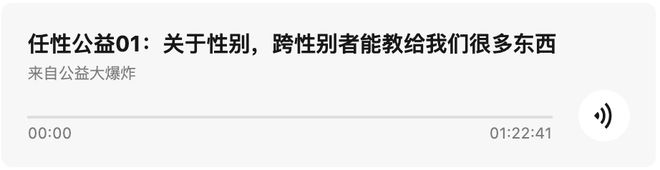
Alexwood
欢迎来到别任性,我是Alex。这是一期特别节目,来自别任性与公益大爆炸和喜公益合作的「任性公益」系列。今天是「任性公益」的第一期,关于跨性别者教给我们的一切。收听平台:| 网易云音乐 | 喜马拉雅 | Himalaya | BIE网站 | Apple Podcast | Spotify | 其他泛用性客户端(如 小宇宙、Pocket Casts)| 搜索 “别任性” RSS 订阅:https:别//feeds.acast.com/任public/shows/性bierenxing(去掉 “别任性” 三字)注:如果你在苹果 PODCAST 上订阅的《别任性》集数不全或者很久没更,那说明这不是正确的 RSS。请用上方这个新的独立 RSS 添加并订阅。如果你是海外苹果 ID,现在应该能搜到另一个新的 “别任性”,是未阉割并集数全的;但如果你是墙内 ID,如果还搜不到,就只能再等等了,或者小宇宙上也找得到。一、跨性别不是“病”,可是......(00:18-13:28)上午11点45分,在门诊时间即将结束的时候,诊室忽然进来了一位中年女人。她没挂号,脸上带着一种坚决,还有焦急,她说,“我们是专门从河南过来的,医生你帮我们看看吧。”十分钟后,补了挂号的女人带着孩子坐到了医生面前,医生拿出一沓资料,在两人眼前铺开,他开始了说过了无数次的开场白:“老百姓啊都认为世界上只有两种性别,男的、女的,是以ta的生理性别为定义的,但是呢,人们发现人的心理状态不能单纯用男的、女的去定义,有一种是生下来是男孩,但坚定地认为自己是女孩,或者相反的……”这个场景来自某家医院的跨性别门诊。这一上午的门诊时间里,除了这对第一次来的母亲孩子,还有近十位跨性别者来挂号,ta们的需求各种各样,有轻车熟路的定期复查,有第一次开激素的咨询,还有面部女性化整形的问询。而在外面的挂号LED屏幕上,诊室正式的显示名称并不是“跨性别门诊”,而是写着这位远到而来的妈妈介绍自己孩子的情况时所用的词:易性症。为什么门诊是“易性症”而不是”跨性别”呢?这两者有什么区别?跨性别是一种病吗?ta们来这个门诊是为什么呢?跨性別(英語:Transgender)是指个人的性别身份认同或者性别表达,与出生时的指派性别不一致的情况,而跨性别的反义词是顺性别(英文是cisgender),就是那些生来的指派性别和后来自己的性别认同是一致的人——对,我们大部分人就是这种情况,而我们这种情况不叫所谓的“正常”,这种情况叫“顺性别”。而“易性症”虽然叫“症”,但易性症也不是一种疾病,它是指“跨性别人群”对自我性别不认同的一种焦虑、抑郁的状态。甚至或许我们可以更简单地说,跨性别是因为天生,而易性症则是因为社会;跨性别者本身没有病,而且也不一定有易性症,而是因为社会的一套性别常规和偏见,使ta们难以接受自己跨性别的身份、自己的身体,使ta们得了易性症。不过话虽如此,跨性别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在很长时间内,还是被当成一种精神病的,而且它去病理化过程很漫长。比如在美国的DSM(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中,跨性别人群的诊断归类分别从1965年的性偏离 (Sexual deviations)到1990年的性别身份障碍 (Gender identity disorders)再到2013年终于迎来了不再带有负面含义的新名称:性别烦躁/性别不安(Gender dysphoria)性别烦躁的表现为,因为性别性别认同不一致而引发的极度痛苦,焦虑,或社会功能失常。需要指出的是,跨性别者不一定就有性别烦躁/性别不安,一个跨性别者也可能非常接受自己身体的状态和自己的身份,社会功能也非常的良好。不过在中国,关于跨性别是否还被当成一种精神病,这个情况就更加复杂一点儿。北大医学部医学心理系博士生韩萌解释:“在国内的诊断标准一直都是那个CCMD3, 还是很老的,以前那个易性症的诊断现在国际上都不太常用了。现在ICD11出来了,已经把跨性别从精神人格障碍里面拿出来了,单独列了一章,叫性别不一致 (gender incongruency) ,所以说跨性别已经去病化了。但是国内就还没有跟上这一部分,所以还是需要 一个诊断,我们才能安全地开激素。”他提到的ICD,也就是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的缩写,叫做国际疾病分类, 现在出到了第十一版。他还提到了一个CCMD3,也就是是中国精神疾病分类方案与诊断标准,现在出到第三版。我也去查了一下CCMD3,在第6部分的第三条:性心理障碍(性变态)下面,找到了“易性症”。这样看的话,易性症这个词,至少在中文语境下,还是带着一些污名的,那跨性别者对此是怎么看的呢?关于这个问题,北京同志中心的跨性别部主管核桃,是这样告诉我的:核桃:“现在我们其实也在做一些事情去推动把这个词给拿掉,因为在最新版本的国际疾病分类,ICD11里面是已经把这个精神病相关的描述都给去掉了,它改成了一个非常中性的词叫性别不一致,然后纳到了性健康里面。我们国家在2015年的5月份,卫健委的官网发表了一个文件,要所有的下属的医院都去学习 ICD11中文版,和使用中文版。但是好像过了一年多,又把这一篇东西给删掉了。然后在2020年的12月,又出了一个新的文件,叫精神障碍诊疗规范2020,然后在这一份新的文件里面,又保留了易性症,你会发现在新的精神障碍诊疗规范里面,很多什么双相障碍,然后什么精神分裂相关的这些条目,都根据最新版的国际疾病分类做了修改的,但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要把易性症给留在那。而且它的描述都是自我矛盾的,在前面又说很多易性症的人有抑郁的表现,但是后来在说你要去评估和诊断一个易性症的时候,你又不能有其他的精神疾病。然后我们也感到非常的困惑,所以我们就给卫建委寄了10封信,然后去要求做一个信息公开,易性症还保留在那里,你的依据是什么?到底是哪个老师编的,需要公开一下。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得好好的跟他们掰扯掰扯。他们给我们打电话了,就是说要尽快回应,对,但是这个是他们逃不开的一个责任,这个是国务院规定,它必须在它的官网上做一个回应。”但是在跨性别去病化的努力中,还有很麻烦的一个困局就是,虽然跨性别不是病,但需要被当作“病”,跨性别者才能够得到所需要的改变。像之前韩萌提到的,在国内他们恰恰需要易性症的精神科诊断,才能够可能从医院的渠道得到激素。很多想开激素的跨儿们跟医生都是这么说的:“医生,我想开药”,而医生也要确定对方已经拿到了易性症的诊断,然后才能开始一系列的流程和问题。所以,即使不是“病态”,但跨性别恰恰要被纳入医学话语之后,需求才能被正视。跨性别者对这种医学话语怎么看?在这个问题上,核桃提到了一个之前被我忽略的角度。核桃:“很多医生其实很能理解跨性别,很能接受跨性别,也很愿意支持跨性别,但ta就是没有办法改口‘患者’ 两个字,因为ta的职业习惯,来的人都是患者,但现在慢慢还是有一些医生会去改口说叫‘来诊者’。说‘开药‘,我觉得也不是什么坏事,因为虽然说跨性别不应该被当做一种精神疾病,但还是被放在了性健康门类里面。如果没有实现完全去病理化的话,它也不是一个很负面的东西,为什么 ?因为首先已经去精神疾病化了,这会推动去污名化,但是它依然保留在一个疾病的条目里面,我觉得这为未来的医保是留了一个口子。如果它完全不在一个疾病里面,你可能连药都拿不到对吧?你又没有什么病,医院凭什么给你开药?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妥协。但我觉得这个妥协是能够换来等价的价值的。”至此,关于跨性别与“病”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有一个比较全面的答案了——虽然这个答案并不是“是/否”那么简单。不过,得到这个答案对我来说,还只是一个开始。一纸“易性症”的诊断后面,还有很多更巨大的问题,比如什么是性别?什么是男人?什么是女人?而这是所有人,包括顺性别、跨性别,都要面对的性别问题。关于跨性别这个话题,它的重要性其实远远不限于跨性别者。跨性别其实是一个对所有人都有启发和冲击的存在,因为ta从根本上否定和撼动着现代社会的一个被当做天经地义的真理—— 就是,性 别是天生的,而且只有男女。 至于如何做男人或者女人,跨性别者因为需要后天做调整才能身心合一, ta们对于性别的思考和体会其实比顺性别者要多得多。所以跨性别者能教给我们关于性别的很多东西,比如你是否好好想过到底什么叫做性别呢?我们在出生的时候,大夫看一眼生殖器,然后就把我们指派为了男性或女性,然后我们长大了,有了个人的社会性别认同,这个认知和出生时的指派性别如果一致,我们就是“顺性别”;而如果不一致,我们就是“跨性别”。而无论是生理性别,还是社会性别,人们都以为只有男和女这两种,事实上,性别类似于一个“光谱”,它的界限并非清晰,种类远大于两种,且具有流动性(fludity)。如果说社会性别是个光谱,可能大家还好理解,比如我们除了男和女,还有跨性别、无性别者,或者性别酷儿,也就是指不认同男或女之间任何一种性别身份的人;在性别的表达上,当然也是个光谱 ,比如大部分人大概都会觉得自己身上同时有所谓的阳刚和阴柔,娘或man的部分。但是,生理性别也是光谱吗?生理性别不是就两种染色体,两种生殖器官么?其实也并非如此,大多数人是XX染色体为女性,XY染色体为男性,但是同时,也有染色体是XX的男性,和染色体为XY的女性,这种情况也被称为间性人(intersex)。另外有人只有一条X染色体,这被称为特纳士综合症;还有人有三条染色体,是XXY,这被称为克氏综合症。所谓的雄性或者是雌性荷尔蒙,也并不是决定性别的绝对指标。一般来说男性体内雄激素会相对会高一些,而女性的雌激素会高一些,而且性激素对于第二性征发育,比如声音、月经、喉结、胡子等等,有决定性的影响,但是这都并不是绝对的,因为性别内和性别间荷尔蒙水平差异可能一样大。比如一些女性体内的雄激素就很高,比如南非的女性田径运动员Caster Semenya,她因为天生具有较高的睾丸素水平而无法参与女子比赛。所以我们并不能用性激素当作某种标准用来划分性别。除了这几种不同的“性别”,还有其他的一些性别相关的概念也经常被我们混淆,比如性别认同、性取向、与性别表达,是三个彼此独立的维度,彼此没有绝对关系,但经常被我们混为一谈。我们举个例子,曾有人问我:如果有一天,你的儿子跟你说我喜欢穿裙子,你怎么做?这个问题我无从回答,不是因为它太难了,而是因为我不知道对方想问什么。而这三个问题对应的就是, 性别表达,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男孩子喜欢穿裙子这件事,它只是一种女性化的性别气质的表达,跟这个人的性取向,也就是他喜欢什么性别的人,是没有直接关系的;同样,喜欢这样表达自己的性别气质,也不代表他在性别认同上就想做女人。当然这个男孩的确可能是gay或跨性别,但仅仅是穿裙子这一点,并不能直接导向这些结论。跨性别者跨的是性别,那这跟性取向,也就是自己喜欢哪个性别的人,也没直接关系。所以跨性别者可能是同性恋——如果说ta的个人认同和喜欢的性别是同一个性别;但也可能是异性恋——比如说他的个人性别认同是男性,而他喜欢女性。当然跨性别者也可能是双性恋、泛性恋、无性恋,等等。我有一位好朋友叫梅森,他是一位跨性别男孩,经过几年的努力,他家人对他的身份已经接受得很好,不过虽然他们对于梅森是跨性别这一点,已经比较清楚了,但是对于梅森的性取向好像还是很困惑。梅森:“但是我爸妈还是觉得我应该找一个男朋友,这件事情我还觉得很神奇,他们没有觉得我既然想要当男生我就应该是找个女朋友,还是很坚定自己的立场,你是我们的女儿你就应该找个男朋友。”Alex:“但他们有没有意识到,现在你找男朋友的话,等于你们是一对同性情侣?”梅:“我觉得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说总是有朋友想要给自己的儿子找相亲,然后经常会有人问我们家,你们家不是有个女儿吗?然后他们就会跟我表达他们在那种情形下很尴尬。然后我就啊?这?这没有讨论的空间啊,就算我愿意他也不愿意啊。”不过呢,很有意思的一点是,关于性取向,梅森也告诉我,在跨了性别之后,他的自己的身体改变了之后,他的性取向的确发生了变化。所以说性取向、性别认同、性别表达这些维度虽说是各自独立的,但是又彼此相连。梅森:“我真的都可以,一直觉得自己是挺喜欢女孩的,但是我后来慢慢的对自己的身体越来越舒服之后,我觉得男生也很不错,而且男性化的身体,男性化的肉体也很不错,所以我觉得,自己会不会是都行。我现在理解的泛性恋就是,你喜欢一个人是不分ta的性别的,你就是喜欢他本人,但是我现在意识到,我喜欢女生喜欢的部分,和我喜欢男生喜欢部分还挺不一样的。所以我还在探索,但我非常确定,自己男生女生都喜欢了。”Alex:“这一点是在跨了性别之后才发生的变化吗?”梅:“对是的,但是我觉得内在的逻辑应该是我跨性别之后,对自己的身体更有信心了,总之是当你学会了自爱之后,你才能学会爱别人。之前我确实花了很多时间在纠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所以没有太想好我喜欢什么样的人。但是我现在在解决了前半部分之后,终于可以花更多的精力在探索我喜欢什么样的人上面。”总之呢,性别也好,性取向也好,弄不清楚,其实也没所谓。你只要知道这些概念,它本身就应该带着这样的流动性就好了。所以根本不用为此纠结,也没有所谓的性取向或者性别认同是错的。如果我们认识到这些概念的人为性,限制性,以及这些人类行为和倾向中真正的流动性,那么人类之间基于性别和性取向的偏见、歧视、暴力和伤害,是不是更加显得无端而可笑了?激素替代疗法是跨性别常用的一种所谓治疗手段,但并不是唯一一种,也不一定是必须的。跨性别需要的医疗项目是综合的,因为跨儿们需要多方位、延续性的支持和干预,所以这中间的医疗项目涉及到多科室、多学科的的交叉合作,这种治疗模式被称为“跨性别综合序列医疗”。比如北京的北医三院有一个易性症综合诊疗团队,它包括以下这些团队成员,第一是精神科诊断和心理咨询团队,他们负责给出测试诊断,心理疏导,和家属的宣教。第二,激素替代和生殖细胞冻管团队,它是由内分泌科、生殖医学科、和男科医师组成的。第三,性别重置手术团队,由整形外科、妇科和男科医师组成,第四,第二性征管理团队,由整形外科耳鼻喉科医师组成,主要针对乳房、喉结、毛发等等第二性征的处理。而在这整个序列中的几乎所有分队下面,都有一个名字叫潘柏林。潘柏林:“我叫潘柏林,在北京大学第三院整形外科医生,我主要是负责跨性别序列医疗专业,现在目前是团队的一个负责人。”潘医生在跨儿社群中人气很高,大家都会叫他老潘。甚至一些得不到父母支持,年轻人会对潘医生有一种特别的情感依赖。关于自己是怎么进入跨性别医疗领域的,潘医生有一个很有趣的段子:“那个时候我身体不好,我妈带我去看道士还是什么,我记不太清了,给我算了一卦,其中我印象深刻就两点,一点是我的幸运颜色是白色,一点是我适合做一些阴阳调和的事情,这两点正好都应验了,白色工作就天天是穿着白大褂,然后也做这种跨性别医疗的事情。当然这个只是个段子,最终其实我主要还是喜欢做一些有需要人去做但是又没有人去做的事情。而且我也不是一个竞争型性格的人,做一些我自己认为也很有价值的事情,自己也很开心,事实证明就我做了这么多年这个事情以后,我觉得这个事情我是越做越开心,就越做越有成就感,有价值感。”除了跨性别医疗相关的技术和知识,潘医生还有一个特别的技能点,那就是对跨性别家长的宣传教育。潘医生:“对于第一次来门诊的父母来说,最多的疑问就是,我孩子是属于什么情况,到底是不是病?第二个问题,ta能不能逆转,是不是可以通过一些治疗能够让ta这种想法就消失,不再有这样的想法。“潘医生告诉我,其实很多来门诊的父母完全不了解跨性别,他们是误以为来这里医生会有办法把他们的孩子“治好”,也就是扭转过来。所以当一位专业权威的医生告诉他们,“你们的孩子没有病,也不需要扭转,事实上需要改变想法的是你们”,这对很多家长来说可能一时间都无法接受。潘医生:“父母的这种认知,这种理解力其实差别很大,有些每一次来都会有更好的认识,更加多的了解,每次来都会有进步,但也有每次来都是为了劝说医生,你不要给ta用药,你跟ta说说用药的坏处什么的,然后甚至还过来威胁一下,每次来都是这样,同样的内容。”Alex:“我之前看到丁香园那篇对您的报道,就是跨性别来访者走了之后,是ta的家长给您扔下个字条,说如果你再给ta开药,我们走着瞧。”潘:“比如说医院层面的投诉,甚至什么公共平台一些投诉,这些其实也让人很无奈,这比写个字条对我们的伤害还要更大。然后你还得去回复,去答复,去解释,可能也会跟你个人的一些考评挂钩的。我有心理准备会经常碰到这样的情况,所以还是尽量劝说,一次不行,我们再说第二次,第二次不行,我们也尽量给ta发一些材料,ta也许不看,但如果说ta哪天心情好了看一看,也许会有更多的理解。”人们对所谓阴阳、男女的观念是如此的根深蒂固,医生能够说些什么才能够松动这些传统的性别观念?说些什么才能让家长真正能够体会或者共情孩子的一些体验?心理博士生韩萌跟我说了一些他的观察。 韩萌:“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性别不就是男和女吗?甭管你是男是女,即便你自己内心觉得是女的,你生理上是男的,那就这么生活呗。为什么一定要变?很多家长很不理解,就觉得性别很无所谓的一个事情,其实我一直想跟这些家长讲明白为什么他们的孩子想变。然后我之前在三院门诊的时候,听潘医生他会这样介绍,本来你是个女生,然后可能你第二天一觉睡醒,你的身体全都变成男生了,你会很难受。然后有的家长他们会思考一下,然后说是挺难受,有的家长可能就不太会去想,就可能会觉得这有什么的,也没关系,然后我自己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会觉得我会觉得,如果说我第二天醒来,我变成了一个女的,我可能也会有那种很突兀很茫然很不知所措的感觉。”但是,要从理念上一下子完全扭转固有的性别观念,接受性别多元,这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与此同时,跨儿和ta们的父母们还有一些更为现实的问题需要面对。这位家长提到的担忧是真实存在的:跨儿们如果选择激素替代疗法或者重置手术,这些手段对身体可能的确会有一些副作用甚至伤害。在潘医生的经验中,有两个实操层面的问题或者担忧,是经常被家长问到的。那就是第一,用激素会缩短寿命吗?都说泰国的人妖活不过40岁是真的吗?还有就是,做了手术之后,如果后悔了怎么办?潘:“激素安不安全,毕竟这是一个药物,而且需要长期服用,是药物总会有副作用。当这种副作用逐渐产生,但是使用者有没有及时察觉,让副作用越来越厉害,甚至造成了不可逆的这种影响的时候,就可能会对健康造成影响。我们临床上做的工作,在跨性别者需要用激素的时候,我们给ta一些合适的方案,同时给ta做一些必要的医学监测,比如每三个月做一次检查,来确保目前用药的情况也是在一个健康的范围之内,一个安全的范围之内,这样的话我们会能把药物副作用的风险降到最低。后悔也是一个经常会问的问题,父母肯定都会担心就用药了以后,比如说发生了变化,胸部发育了,声音变粗了,等等这些,出现了以后又不可逆了,ta将来后悔怎么办? 其实只有ta自己并不是很明确的时候,才有可能会说,这些变化过一段时间以后我不想要了,如果这个人很明确有易性症的话,基本上往异性方向的性征转变,是ta毕生追求的一种愿望。一般来说是我们很少见到有后悔这种情况。”在整个跨性别序列医疗的项目中,性别重置手术可以说需要的门槛是最高的,而且前期需要心理咨询,激素替代治疗的尝试,还有需要提供各种国家规定的文件证明,这些的目的都是为了系统化的排除没有想清楚是否接受手术的人。但是在中国需要性别重置手术还有多一层的门槛。北京同志中心的核桃给我详细的讲解了一下相关政策:“做性别重置手术,说实话还挺还挺难的,而且需要的东西非常多,但我指的是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明文规定的,也就是只能管到中国大陆地区的这么一个标准。第一你需要年满20岁,然后这个就很奇怪,因为我们绝大多数都认为18岁就已经是成年了,但是为什么偏偏是20岁。第二个是你必须要有易性症的证明,易性症的证明又必须在三级以上的精神科的医院或者医生开出来才有效。那么可能很多小城市的还得专门跑到一个地方,而且有的医院开出来的不是易性症三个字的话,他还不认,你必须清清楚楚写着三个字才可以,那就很麻烦。每个医院的规定可能又不一样。比如说有的人知道说北京能开,然后跑到北京来,结果北京有的医院说我要观察里两年或者一年才可以开,相当于就白跑一趟。所以在这样很混乱的情况下,大家很容易跑错地方,或者是说要反反复复跑好几趟才能开到证明。第三个是我们认为最苛刻的一个标准,那就是需要你的父母的签字,原文叫需要直系亲属的知情。虽然好像听起来说,你只要告诉你的直系亲属就好了,但是在实践的过程当中,它不仅是需要你的直系亲属,也就是你的父母要要同意,还需要把这个同意书拿去做公证。这个就相当于就非常的复杂,那你就不可能说只是打个电话告诉你父母这么简单,孩子还得领着你父母去公证处,而且也不是所有的公证处都可以做这个文件的公证,我了解到北京就那么两三家,上海也就那么一两家公证处可以做。而且不管你20岁、30岁、40岁、50岁,只要你的父母还健在,你想去做这个手术都需要这样的公证文件。如果说你的父母过世了,那好,提供你父母的死亡证明。”听起来在国内跨性别相关的政策和规定上,父母对跨儿们进行转变和医疗的决定有着很大的干预权,甚至控制权。这是为什么呢?我也向潘医生请教了这个问题。Alex:“因为我们一般认为18岁以上就不需要父母同意了,那为什么跨性别手术还有这样一个措施呢?”潘:“这其实是最后一个阀门。性别重置手术,它其实是一个破坏性的手术,而且是一个风险很高的一个手术,不可逆的手术。所以一旦做了以后,如果万一再后悔,那是绝对回不去的了,没有任何办法可以回去的。所以这个是对于我们来说也是慎之又慎。 至于父母知情这个问题,国家制定这个条文我是能理解的。因为如果说这孩子根本不跟父母讲,然后就直接来做了手术了,其实是会引起一些家庭伦理上的一些隐患,我是可以理解。但是这条条文对跨性别者来说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因为因为如果说父母对跨性别这个问题很不理解,完全不表示同意的话,ta可能就这一辈子没有机会做手术,但是目前我们也只能按照这个来进行。”潘医生提到的这个中国特色,或许还有更深层的一些文化因素,比如核桃对于中国的酷儿需要面对的独特的一些家庭关系的困境,是这么理解的:核桃:“我觉得整个中国的社会还是基于一个大的家的文化背景下, 就会有传统的宗族观念,比如说你忤逆了你的父母、伤害你的身体,都是不孝。你要去做这个所谓的性别重置手术,那是一种所谓的生理上的‘阉割’,然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又是一种不孝。可以说跨性别这个身份把所有儒家认为不孝的标准都占尽了。” [录音:与父亲断绝关系的跨性别在门诊咨询脸部整容]听到现在会不会有那么一点父母皆祸害的意思了?现实中开明的父母当然也是有的,暖心的故事也有不少,比如下面这位跨儿的妈妈,她叫简。她的孩子是一位跨性别女孩,但是她可能不算一位最典型的跨儿家长,因为她对孩子情况接受的相对比较快,而且家中也没有因为这个事情发生过比较激烈的冲突,而简相信,当没有了和家长的对抗,她的孩子才有更多的空间去思考自己的身份和感受。不过即使如此,在简刚开始得知孩子的跨儿身份的时候,还是感到过非常绝望。那是为什么?我们也听一听家长的角度吧。简:“它是一个过程,刚开始的话是特别震惊,因为这个概念对于一般家庭来讲,我相信大多数的人不会特别去了解或者去接受。听到后我先查了一些资料,首先是觉得不太相信,然后随着她不断的坚持,似乎确认她的确是这这样一个情况的时候,又特别绝望,你知道吧?那种绝望就好像这个孩子整个人生就毁掉了。本来自己就是辛勤培育的一个很好的茁壮成长的一个孩子,然后对未来有充满着无限的想象。最关键是觉得说她就会从一个社会的大群体中隔离出来变成一个小众的群体,那么就相当于她失去了一个很大的世界。”Alex:“当时您有尝试过想让孩子矫正吗?或者是希望他改过来?”简:“当然希望,我觉得可能每一个家长都希望,因为我在北同的一个群里,这个群里头很多都是跨性别的家长,其实每个家长都抱着这样的希望,希望孩子能够从跨性别这个概念里面出来,但是好像这种希望是有点像期待奇迹出现一样,几乎是不可能的,只是我们自我的一种安慰。”简:“坦白说会有。会觉得她会过的比较难。因为她会面临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你吃了激素以后,你身体会有各种变化,对吧?然后你即使做了性别重置手术以后,那么手术也是有风险对吧?那么做完手术以后,你从本质上来讲,你依然不是一个完整的女性,你没有子宫,你没有正常生殖能力,你是其实还是不能完整的去体验女性的生活的。”简的担忧和其他父母的很相似,但是不同的是她对孩子的关怀,带着一份难得的同理心,所以比起自己的担心和焦虑,她选择更关注孩子的精神状态,以及如何能够给到她支持,而不是如何去控制她。简:“她大一前半学期情绪是非常不好的,也会自己在被子里哭什么的,自己也很难接受。另外一个就是,ta们学校发生的一件事对她触动还是蛮大的,她隔壁的宿舍,也是有一个跨性别的小孩,家里不接受不支持,就自杀了,所以对她的情绪影响也是很大的,所以她那个学期学习成绩也很一般。所以她还是背负了很多压力的。我反而希望说我们做家长的去更多的去了解,去更多的帮ta们去分担,是吧?能够帮ta们去想到办法去应对,我觉得这是我们应该做的,现阶段我希望她能更多的先去接受自己,而不是在一直对抗。”那么对于简这位母亲,她想法改变的关键点又是什么呢?她说虽然这个过程是循序渐进的,但是的确有两件事情对她冲击很大。第一件事情就是她自己的心理咨询师和ta说过的一句话。简:“后来我遇到一个心理医生,刚刚好是和性少数群体的接触是比较多的,ta告诉我说,这个群体其实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少数,其实是人数是很多的,然后ta们的生存现状是怎么样的,然后我才知道说我们这不是一个异类,或者好像是什么特别奇怪的事情,其实真的已经存在了,而且存在很也有很多人的这样一个群体。第二个转变的话就是和北同的联系,ta们有很多的活动,包括给跨性别者维权,还有基金会的成立,让我接触到很多不同的跨性别的活生生的人群,我才感受到说原来这个世界的有一部分人的生活状态是我们所不了解的,而ta们也实实在在的生活在你的周围。”简提到的北同就是北京同志中心,提到的基金会是指潘柏林医生在2020年专门为跨性别创立的栢林基金。而潘柏林孜孜不倦地对家长的宣教,其实除了之前他提到的政策和规定相关的原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父母的理解和支持,其实是孩子精神状态和对身体接受状态提升的重要因素。现实中很多本该是最爱孩子的父母,却成了跨性别者实现身心一致的道路上最大的阻碍。我的朋友梅森在还没有开始修复他的家庭关系之前,面临回家过年这件事情的时候,有很复杂的情绪和挣扎,他还特意去心理咨询师那边做了心理建设,以防回国之后可能面临的危机。梅森:“我激素7年,但是我前4年基本上是家庭关系是没有任何改善的,因为我没有回家,我在外面读书。你知道我刚回国的时候,我是把护照不带回家的,会把护照放在一个朋友家里,说如果我如果我什么被软禁了什么的,你一定要拿着护照来接我之类的。当时非常的紧张,就是我听过太多那种恐怖的故事,然后就会给自己留一个后路啥的,真的是鼓起非常大的勇气才决定回到国内的。”到了这里我渐渐意识到家长的不接受可能恰恰是导致易性症的原因之一。家长越是不接受孩子的易性症就越严重。而相反如果家长能够接受孩子的跨性别身份,易性症的症状其实也会减轻。简:“一开始的话,孩子其实也是很迷茫的,她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时候她肯定先会藏着掖着。然后包括她的衣服,她会经常是藏起来不让我们看到等等。但是后来大家坦然沟通以后,我觉得最大一个变化是我们更关注她的感受了,而不像以前一样,因为家长都会有这样一个惯性,因为你从小生下ta,你就会有种惯性,总觉得说,她要听你的安排想法。但后来就会觉得说生命个体的体验原来是那么的不同,你就会更关注她的感受,比如说以前我肯定习惯叫她儿子,她说我不太喜欢这个称呼,我说怎么称呼?她说你可以叫孩子,我以后就很注意,我不叫儿子,就叫孩子,就从一个很小的点开始吧。”简的思考和观察,在心理学博士生韩萌这里也得到了印证。韩:“我也见过很多家长比较支持孩子发展,这个时候这个孩子自己的力量能发展起来之后,ta会去追求很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并没有就说要立刻把性别置换手术做了。ta们如果被得到了支持之后,ta们会把兴趣点转向,之前有一个我访谈过的妈妈的孩子,ta就特别喜欢学化学,然后ta就在家里搞了一个自己的小化学实验室,然后一直在去做自己的各种各样的化学研究。ta也并不一定执着于一定要去立刻做手术,是因为你越压制ta,ta就越想要用那种更直接的方式去转变。然后如果你支持鼓励ta的话,ta其实是可以一步一步来。”这一点非常有意思。所以跨儿们追求的身心合一,可能并不意味着ta们一定想把自己的身体变成某种符合生理性别的样子,事实上也如此,很多跨性别是能够接受自己的身体的,而甚至不选择任何激素或者手术的干预,并不是所有的跨性别者都会经历性别烦躁或者性别不安。其实对跨性别的真正接受,并不是说你允许ta去做手术,而是说你允许ta不做手术。对跨性别的真正接受是指允许一个人拥有不符合传统意义上男或女的生理身体,并且对自己身体感到舒适接受,而不会因为常规和标准去改造它,或者有改造它的焦虑。而这样一个想象,并不限于跨性别,甚至不限于性别本身。我们能否对身体有这样的一个想象,这是我在这期播客里想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在下面的第四部分,也就是最后一个部分中,我会谈谈跨性别对我们所有人的性别启示。四、对所有人的性别启示(53:28 - 1:22:20)
潘医生:“其实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手术诉求的 ,很多人如果说只是出柜,只是外貌上的改变,不做手术也可以的,比如说通过梳妆打扮或做一些面部整形手术等等,甚至用一些激素,完全在外观上就能够达到一个很接近的状态。也有些人对生殖器官是很厌恶的,这样的完全不能接纳这种情况下,可能需要性别重置手术,或者说,她最终需要更改身份性别的,也是基于目前的国家的法律规定,ta需要进行性别重置手术。”Alex:“所以您遇到过仅仅是为了修改身份证而选择做手术的吗?”根据北京同志中心发布的《2017年中国跨性别群体生存现状调查报告》,51%的跨性别者有性别重置手术的需求,其中跨性别女性和跨性别男性的手术需求达77.8%和56.2%,但总体上仅有14.8%有手术需求的跨性别者进行过性别重置手术。对一些跨性别来说,即使没有经历性别重置手术,也能达到对外表的良好感觉,至少可以接受。这个状态叫跨性别一致(transgender congruence)。比如北同的核桃,她是一名男跨女的跨儿,在伪装钢铁直男的中学时期曾非常厌恶自己的身体,现在用了几年激素,手术也没有做,但面对同样的生殖器,却可以与之共处了。核桃:“在我的青春期刚刚开始第二性征发育的时候,那个时候是非常焦虑的,非常想要去做这个手术,尤其是在那种夜深人静的时候,那种焦虑会突然感觉就是从你背后蹿上来,然后你整个身体都觉得要跟自己剥离开那样一种焦虑,然后你就真的看到自己的器官好像就很想去捏烂它,或者用什么东西砸烂它,或者用菜刀就切掉它,会有那样的焦虑。但是第二天你去上学,因为我在重庆当时最好的中学上学,压力很大,每个年级2000多个人,然后可能你瞬间就要进入一种内卷的状态,一种竞争的状态,你就又会马上忘掉这种事,然后你回家一个人的时候又会回到这种状态,就在这种状态中反复的循环。但是随着这个人的成长,随着这种对于性别的理解的加深,好像有的时候又没有那么的焦虑的想要去做这个事情。尤其是接触了更多女性主义的一些思想过后,开始对自己的性别做一个解构,就是开始去反思,我为什么一定要有一个在男权审美下的身材,那么一套器官,我才是一个女性,为什么我是一个女性,我自己不能说了算?然后以及我周围的这些同事,也主要就是做lgbt的这些同事都非常尊重我的身份,不管我做不做手术,ta们都以女性的身份来看待我,那么慢慢的这种焦虑好像在获得了他人的认可和达到了这种自我的理解或者和解过后,你会发现这种焦虑在慢慢的褪去。我也不是说我这辈子可能就不做手术了,只是说这个事情变得不急了,可能等我那一天就是钱赚够了,然后也有空闲的时间了,可能抱着顺便去旅游一样的心态,也许吧。”这让我思考,是不是“身心合一”本身这个概念就是松动的、不稳定的、极为主观的?当身心合一失去这种主观性和灵活性,而变成了一种生硬的规定和要求——比如说你是跨性别可以,但是你得努力让自己生理身体和社会性别得对得上,才能在社会和法律层面上被接受——如果是这样,那无非是另一种压迫和歧视而已。简的孩子现在19岁,她已经明白了这个现状。简:“她现在的阶段是吃药物,性别重置手术她其实并不急于做,甚至说不做,她是完全可以接受自己的。但是面临将来社会性别角色的一个问题,比如说你将来去旅游,甚至去泡温泉, 你在外面去男厕所还是女厕所,这些问题都会是困扰她的问题。所以就是说性别重置手术更多是为了去适应社会的规则而不得不做的一件事情了,所以我心里有个愿望,自己虽然说没有能力去实现,但是特别想呼吁我们有关的这样的一个社会力量,如果我们社会足够开明的话,这些孩子是可以有更多的自由的空间,而不是被社会这种所谓的文明或者规则所绑架,必须做伤害自己身体的事情。”可见,社会对于两元化性别的巩固和管控是渗透在各个层面的,即使跨性别也得进到男或女的小盒子里。这显然是一种懒惰的做法,但二元的确比多元要简单多了。而面对着渗透在社会法律、文化、人际交往、社会常规等等层面的性别二元论,大多数人也只能选择顺从和屈服。核桃也提到,跨性别姐妹们内部,对身体的想象和性别和理解也非常不同,有的人可以以一个非标准男性或女性的形象生活,也有人则用更严苛的性别外形和身体标准要求着自己。核桃:“也有最极端的跨性别(女性)可能不仅仅是要完成一个生殖器的再造,她可能还要去隆胸,要去整容,要去做声音,要去做一个大全套,而且可能所有的东西都做了过后,她还是觉得不满意,因为她的性快感可能没有顺性别女性那么强烈,她也不能像顺性别女性那样去来月经和怀孕,所以你会发现大家对于这种身体的想象,对于性别的理解是很千差万别的。其实这么看的话,跨儿们跟顺性别者经历的性别和外形焦虑是完全同构的,身高、体型、胸围、发量、体毛、脸蛋,只是这一切相关的外形焦虑可能对于跨性别者会更突显,因为对顺性别者,这些问题只是关乎你够不够好看,但对跨性别者,这些是关于ta们够不够被人当作那个自己认同的性别,也就是,能不能pass。梅森:“Pass的字面意思就是你可以通过社会对你的评判,我可以神不知鬼不觉的混入顺性别男性的人群中。”梅森说他基本上用激素6个多月,在外形上就可以pass了。对跨性别女性,如果想达到一个所谓标准的外形,挑战就会更多一些。比如身高是没法改变的,而且雌激素对每个人的效果也不一样,但是如果你在外形上不能pass,就意味着你可能需要承受更多的社会风险。核桃:“所以你说的这种情况我觉得它也是两方面,一方面是这种外界的文化在打压,如果你不符合这种社会的规律,你在外面可能就会引来更多的目光。你去上自己认同的卫生间,可能就是被赶出来被骂变态,甚至可能会被抓起来,或者被示众或怎么样,在学校可能会被霸凌,在职场可能会被开除。确实有这样的,但是也会有一些跨性别,ta会内化这样的社会的规训,ta会觉得说如果我去违逆了这套规则,我就活该被惩罚,或者我就很有可能被惩罚,ta自己可能也会非常刻意的去装扮自己。这样是忽略了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整个社会结构性的对于跨性别群体的压迫,有人认为说一个跨性别者不被社会所接纳,是ta自己不努力,是不努力上学,不努力工作,不努力去成为一个男人或者女人,但是ta们没有意识到,其实这个社会本身就限制了很多跨性别公平竞争的机会, 很大程度上是从根本上就切断了跨性别以一个正常人的身份去生活的这种渠道。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还用一套社会的这种这种广泛的这种价值去要求ta,我觉得这是不公平的,也是不负责任的。”说到这里,我要强调的是,我当然并不是说跨性别者所做的形象上的努力跟改变都是被迫的。事实上跨性别者在身体上能够呈现出自己认同的性别的外貌和形态,这对ta们来说是非常愉悦非常解放的事情。但是我们也需要考虑到做这种转变的所谓的外形标准是什么?是从哪来的?我们是否又真的需要完全的去遵守它,或者要遵守到什么程度,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选择不去遵守吗?下面是核桃讲述的自己的转变过程,从中学时期的极度压抑,到大学后第一次易装,直到现在找到了自己心目中理想的女性的样子。 核桃:“对,肯定从小学就开始想。但是你不敢这么去做,因为你这么去做,是对自己男性气质的一种瓦解,比如说跟女孩跳皮筋,你会表现出一种无奈,说我就是不得已被拉过去的我才玩,我是被迫的,但其实你就是想玩,但是你要演成那个样子。所以你会发现我出柜之前,我这十几年中过得很累。我觉得一开始我是特别好的,因为可能在小学和初中的时候,我家里姐姐特别多,然后我家这种男性的这种角色也是比较缺位的,所以那时我觉得我还是挺乖巧可爱的一个人,但是到了高中,开始上什么UC啊什么贴吧那些东西,然后就真的被一些男性的东西洗脑,教你怎么去鉴别你的女朋友是一个荡妇还是一个就是忠贞的女人,网上当时真的好多这样的,给这些直男的指南,然后我就觉得我慢慢被教化成一个非常刻板的男性。然后上了大学,然后开始慢慢接触这些性别相关的东西,开始去正视自己跨性别身份,我才慢慢又开始开始去反思我之前的那些想法。而且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我高中的时候,我自己就是一个非常恐跨的人,我自己会觉得自己是一个不正常的人,我觉得很难理解我为什么会有这么糟糕的想法,然后是我都不敢告诉任何人,我有的时候特别想去成为一个女生,我有的时候会非常的焦虑,感觉自己的身体快要崩溃掉瓦解掉那种感觉。但我在外面又必须撑起我一个正人君子一个钢铁直男的形象,我觉得我甚至还跟我的同学发表过一些恐同恐艾(艾滋)的言论,我现在想想起来,我真的觉得当时自己好蠢。 我记得应该是19岁的时候,真的就是因为一个人的一句话,一下子我感觉我整个十几年的伪装都被击溃了。ta自己是个跨性别,然后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程序员,然后会坐地铁,下班,然后去一家喜欢的卖小吃的店,买一点小吃带回家,然后住的地方就非常的北漂。然后你会发现一个跨性别的生活竟然这么的平凡,你就会觉得说,原来一个跨性别是可以过上平凡的人生的,然后ta也告诉了我一句话说,就是跨性别不是精神病,我觉得ta这个人和这句话真的就一下子把我击穿了,我就觉得我这十几年的伪装是为什么呢?做真正的自己也是可以过得很好的,至少过上一个平凡的人生也是可以的。我为什么还要去费心费力的去伪装,去过我不想要的生活去做我不想做的人?然后我就开始尝试。我开始去化妆,然后穿戴假发,穿裙子,然后招摇过市。我记得当时还引起了我们学院的一点小小的恐慌, 专门开会去研究了一下怎么处理这个事情,但最后也没有真的处理。第一次出门最大的一个情绪应该是激动,然后才是有一点这种担忧,因为当时也是晚上,然后你会发现夜晚好像就带了一个滤镜,你的一些细节会被模糊掉,然后别人一眼望过去,你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生,然后你就会有一种错觉,好像你就真的以一个女生的身份融入到这个社会当中了。你走在路上,一个快递小哥,一个外卖小哥会停下来问,小妹妹你知道这个地方是哪里吗?那一瞬间你就觉得,我竟然可以被当作一个女生去看待,那种心情是相当激动的,而且那种放下你十几年的这种戒备,这种压抑,突然一下子释放了过后,真的你会有一种从瀑布上掉下来的感觉,一马平川了,就是那种释然是很舒适的。然后你就疯狂出门,疯狂去见一些朋友,然后因为这个事情太开心了,你真的不停的想要去尝试。但是我好像刚出柜的时候,我又是一个非常刻板的女性,每天都在焦虑自己的体重,自己的腰,自己的腿,我觉得自己腿又弯,又没有腰没有胸,没有屁股,穿衣服不好看,每天都在焦虑这些事情,然后出门也一定要化妆,一定要抹口红,一定要弄下头发就用卷发棒弄一下。然后慢慢你会开始思考,女性真的就只是这样吗?我发现我自己更喜欢或者说更倾向于成为一个专业的女性,有专业技能的女性,有自己独立思考的一个女性。我就开始去更多的关注自己的内在,比如说通过摄影,然后有一些艺术上的想法,一些表达,你会发现有了这些东西过后,它会充实你的灵魂,然后你会慢慢的去忽略掉,或者说不再在意你外面那些东西,像现在我就很少穿裙子出门了,因为你穿裙子真的很麻烦,你的坐姿然后都需要去考量,然后包括有些裙子很紧,可能你都没有办法以一个舒服的状态去工作。然后真的就开始变的实用主义,然后包括觉得摄影可以让我有一个专业的一个形象,或者说摄影需要一个专业的形象,我可能就会为专业的形象去服务,把自己穿的简单一点,大方一点,然后适合这种在外工作的这种穿搭,去呈现给世人。我不会说我是从一种女性变成另一种女性,我觉得我可以是很多种女性。我可以随时去把自己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向去打扮,我觉得人永远不要把自己框在一个篮子里,对吧?”所以你看,顺性别也好,跨性别也好,在对自己的性别气质的探索上,其实大家没有太大的不同,我们可能都会经历这样一个过程,你可能不喜欢自己的样子。那么你想成为什么样子呢?而且你想成为的样子的标准,它又是真实的吗?还是又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虚构?既然如此,我们有可能从这种种的常规中突围,最后成为所谓真正的自己吗?相信很多来听别任性的朋友都会对性别二元或者刻板的性别印象已经有所反思,而且自己也会在追求一种非两元的性别表达。凯特伯恩斯坦在《性别是条毛毛虫》这本书里说,“我知道我不是个男人,渐渐的我明白,我很可能也不是个女人。问题是我们生活在一个要求我们非男即女的世界里。”性别气质也是一样,阴柔、阳刚、娘、man这些性别表达和二元性别深深的绑定在一起,让所有人包括顺性别者也深深的受困其中,我们所有人的生命体验可能都因此贫瘠暗淡了很多。更糟糕的是这种二元的性别结构和性别表达也与性别歧视深深绑定着,在男女阴阳二元里,男优于女,阳优于阴,两者并非平等地共存,而是存在着等级,反而又巩固着性别二元。因为二元结构一旦被打破,男性的性别红利也会受到撼动。核桃开始从男到女的转变后,感受到这种社会地位的下滑,她还听过一个男跨女朋友的故事,因为不再是儿子,家里决定,她死以后,就没有资格进家族的祖坟了。其实打破性别二元不是新的概念。你可能听过“酷儿理论”这个词。“酷儿理论”其实内部涵盖了很多迥异的理论,但如果一定要抓一个重点,那就是“性别没有任何实在的本质,是操演的结果”。由此衍生出的性别实践,就是打破二元性别结构:不是男就是女。但是也有跨儿们在勇敢而不断地冲撞这个结构,虽然可能尤其困难,比如住在北京的圈姐,心理博士生韩萌这样描述第一次见到ta的场景:韩:"应该是之前咱们北同那边有一位叫圈姐,是留着胡子,然后画着很浓的口红,然后明显的是男性特征和女性特征都有。然后我在第一眼见圈姐的时候,我当时是内心有一些冲击的感觉的。最开始的时候我也不明白,因为其实我自己认为我是没有这种偏见或者歧视在里面的,但是我当时那一下确实我还是会好像我是没有经过大脑的,就是立刻会有一个这样的不太舒服的感觉。我后来再去看文献的时候,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文章,讲到就是说人们对性别会有就是一种生活中习惯化的这种二元性别的这种检索,就相当于你通过这个人的性别的信息来去和ta去沟通去交流,比如说如果你看到这个人是个男的,这个时候你就会知道,如果我也是个男的,我就知道我们是同性,我就会比如说可能跟他的这种人际之间的交往的会有一种模式,或者会有一种习惯化的一些方式,会让我们觉得都比较舒适的方式。如果这个人是一个女性,我可能和一个女性去相处的过程中,我也会保持一定的这种异性之间的模式和距离。但是当一个人好像你很难界定ta是男是女的时候,可能你在和ta相处的时候,你会有那种局促的感觉。”韩萌在采访结束后还特别担心自己说的话会不会冒犯到圈儿姐,但我觉得他完全不必担心,因为圈姐就是想让人不舒服,当然也是因为圈姐自己喜欢这样打扮,但另一方面ta是有意识的用自己这样的形象去刺激大家的思考,去冲击一些大家习以为常的性别互动。圈姐曾经在一场活动上说,ta的生活就是一场与性别的搏斗,而普通人还没有这个机会。简:“ta应该也不是跨性别男,也不是跨性别女,ta是好像属于那种酷儿。我理解的就是你看ta穿的衣服是比较女性化的,但ta留着胡子,涂着指甲,涂着口红,一开始见的时候你会觉得怎么会这样会,有点奇怪是吧?甚至有点害怕。但是你跟ta再去做多一些接触和了解的时候,你会发现ta真的很热情,然后ta也很坚强,ta面对那么多这种质疑的眼光,ta很勇敢地做自己,很自信。所以你会觉得,虽然ta们会经历这样一个跨性别的困扰,但是生命的那种力量和生命的那种光芒依然不会遮掩 ,反而因此会焕发出更多的那种生命的这种火花和生命的热度。”其实圈姐这样子的非二元的或者性别流动的状态,是一些跨儿们向往并追求的,但在现实中,做一个留着水晶指甲的男人,或者做一个留着胡子的女人,这都太难了。因为做先锋是有巨大的消耗的。当你每天被社会看作怪胎,每天要接受那样一种异样的目光,但你还要保持抬头挺胸骄傲的走在路上,可能真的没有几个人能做到,所以虽然在简看来,圈姐是一个跨儿偶像,一个榜样,但是她会希望自己的孩子也那么出格吗?还是在以后的人生里就做一个普通人?简:“我们都希望把孩子培养的很优秀,对吧?我们在孩子身上也倾注了非常多的精力,是吧?我们肯定是希望孩子出类拔萃,对吗?但是有的时候发现这种问题的时候,你会忽然觉得说我希望她哪怕不这么出类拔萃,哪怕她活得极其平庸,我希望她按照一个普通人那样生活。那个时候你觉得你面临一个巨大的失去,因为你觉得失去了常人所拥有,而你有可能是无法拥有的一些体验和生命的完整,你肯定会这么想,我当时肯定也是这么想的,但后来我越来越不这么想了,不这么想的原因是什么?我觉得第一个很多东西你是没有办法选择的,对吧?你的智力,你的身材,你的样貌,你的有的选吗?你没有的选,那么我们既然已经是社会多样性或者生物多样性的一个体现了,我们没有选择的情况下,我们要怎么办?我倒希望ta能活出不同寻常的自己。所以有的时候我倒觉得孩子的这种变化,是带给我很多更深刻的人生的思考的,所以我真的希望ta能够去接真的去接受自己的这样一个身份,然后坦然的去接受,同时能够为跨性别这个群体做一些事情,也能够让这个群体看到更多的希望,因为就好像圈姐让我们看到希望一样是吧?我们知道还可以这样活着,其实每个人都可以把自己活成一面旗帜的,哪怕不是别人的旗帜,也可以是自己的旗帜。”跨性别给所有人带来的启发,或许除了冲击二元性别,鼓励多元表达这些性别理解之外,还有一种重新看待生命的方式,跨性别不需要被包容,因为它的存在本来就没有错,我们需要做的是和跨儿们共同面对一样的性别难题。我们没有选择性别,但我们可以选择不让性别完全定义我们。我最后问简有没有想对孩子说的话,她的回应无意中给跨儿这个词提供了更多的一层含义:性别问题是生命中的一个难题,但是也是可能遇到的众多的难题之一而已。跨儿跨越了性别。这份强大或许也会帮ta们跨越更多可能面对的困境。简:“我是觉得给孩子还是志存高远,让ta能够有力量去跨越这种遇到的这些沟沟坎坎,而不是说遇到一个小的石子小的水坑,然后跌倒就爬不起来了,我不希望我的孩子是这样的,因为即使不是跨性别,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对吗?我们现在抑郁的小孩有多少?跳楼的小孩有多少?希望ta真的能有一个更强大的内心,强大是说足够的对自己的价值的认同,而不是说仅仅是一个性别的认同,就把它当成一个问题而已,我们解决了它,继续朝前走。”主播:Alexwood
调研:Alexwood;李幸倍;刘昊
脚本:Alexwood
采访:Alexwood
采访协助:李幸倍;刘昊
剪辑:Alexwood;李幸倍
声音优化:李幸倍;Tong
文字+排版:李幸倍;顾芳洲;Alexwood
头图设计:冬甩
音乐:
Forensic Patterns by Philip Guyler & Paul Clarvis
Nuance by Paul Mottram
Better Future by Josh Oliver
Rising Tides by Lucas Cantor, Dan Martinez & Thomas Parisch
Hopeful Progress by Paul Mottram
Sandman by Stefano Civetta
(all by courtesy of Audio Network)